黑道悲情第一部33歌词由周建龙&中广影音演唱,出自专辑《东北往事之黑道风云20年1:古典流氓丨周建龙演播丨孔二狗丨热血黑帮犯罪》,下面是《黑道悲情第一部33》完整版歌词!

黑道悲情第一部33歌词完整版
从家里出来以后,
李灿然到了江边。
江边已经有了七八个西郊的悍匪在等着他。
这些人里面,
老五、
房二、
土豆都在,
全是李灿然过命的兄弟。
李灿然话不多,
但没一句废话,
一共只说了三句。
在这个下着毛毛雨的漆黑的阴天的春夜。
他的每一句话都能让人不寒而栗。
人活一口气。
树活一层皮。
我这口气还在。
完蛋的肯定就是他东霸天。
听说他跟陈白鸽那***结婚了?
那***谁想碰就归谁,
都想碰就一起上,
不管谁是第一个,
我是最后一个。
我恨一个人。
我让他热。
说完,
李灿然径直朝那条现在早已经拆毁了的破桥走了过去。
这七八个人紧紧的跟着李灿然。
走在李灿然左边的是老五。
走在李灿然右边的是土豆。
他俩的共同点是每人提着一桶柴油,
桶是那种可以手提的打散白酒的桶。
八九双黄胶鞋踩着有些泥泞的马路,
从西郊一直走到了大东边儿。
距离至少有十几公里,
愣是一步没停。
这群西郊出来的泥腿子,
个个都是神行太保,
一个比一个能走,
而且连西都不用歇。
为啥不骑自行车呢?
答案很简单。
没有啊。
尽管可以有,
但是真没有。
或许偶尔有两三家有自行车,
但那也是家里最大的财产,
怎么可能打架带出来呢?
一旦被****抓到,
那连自行车都会被没收的。
人抓进去判上个几年,
他们可能不在乎。
但是自行车要是被罚没,
他们得伤心至死啊。
东霸天说过,
穷人失去的只是锁链,
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。
这个定理马上就要在他自己身上验证了。
西郊这群连锁链都没有的混子们,
来跟他争夺整个世界。
这场春雨越下越大。
到了后半夜,
李灿然等人到了,
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瓢泼大雨,
而且还时有春雷。
这八九个落汤鸡似的过江猛农在养母家的墙外面开了个小会。
就是这价。
没错。
老五很肯定。
是左边那间呢,
还是右边那间呢?
老五一脸茫然。
这个不知道。
老五还是这么可爱,
李灿然真恨自己,
为什么居然还相信老五的能力,
还让他来打听,
要是扑错了房间,
打草惊蛇了怎么办呢?
今天李灿然来,
就是为了给东霸天点天灯的。
啥叫天灯?
以前呢,
西郊这群混子无聊的时候在野地抓一只大眼贼,
就是田鼠,
抓到以后,
大晚上的给他浇上煤油,
点着了以后放他跑。
然后这只大眼贼就是在剧烈燃烧中高速奔跑,
死亡,
惨死。
这就叫点天灯。
李灿然恨东霸天,
就让东霸天热。
李灿然向来喜欢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
他让我冷,
我让他热。
在过去的100多天中,
桶柴油泼在冬霸天山上,
然后点着了的景象,
已经在李灿然的脑海之中浮现过无数次了。
李灿然继续问。
家里有狗吗?
老五继续一脸茫然。
不知道。
我操。
李灿然快被老五折磨疯了。
怎么了?
老五哪是小可爱呀,
分明就是个可爱多呀。
李灿然没有再搭理老五,
两块石头扔进了院,
院里没狗叫。
老五也捡起了两块石头,
作势要使劲扔。
你嘎。
李灿然压低了嗓子喊。
啊。
砸玻璃嘛,
不是。
我操,
放下。
李灿然气得肠子都疼啊。
本来肠子就不好,
哪经得住老五这么气呀。
啊。
老五挺不情愿的放下了石头。
他挺无辜啊,
他不知道为什么被骂,
他憋屈啊。
行了,
进去再说。
李灿然一挥手,
八九个人齐齐地翻过了大墙。
呵,
这房间居然连窗户都没关,
看来是杨五昨天喝得太大了,
外面现在又打雷又下雨的,
他竟浑然不知。
李灿然趴在窗户上认真地看了许久,
确定了左边的房间堆放的是杂物,
右边的房间里的炕上有人躺着。
李灿然等人再仔细端详了一会儿,
右边的房间内,
炕上有人躺着,
就一个脑袋。
李灿然又是一挥手,
带着三个人就跳了进去。
房二拿斧子,
老五和土豆俩人提着柴油,
房二的斧子架在了杨五的脖子上,
完全采用和几个月前东霸天同样的做法。
可这杨五居然还睡得跟死猪一样,
根本没醒的意思。
李灿然压低了嗓子,
同时捂住了杨母的嘴。
姓冯的。
起来。
嗯。
杨五睁开了他那小绿豆眼儿,
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呢?
老五已经往杨母身上浇柴油了,
李灿然才忽然发现,
自己按住的这个人不是东霸天。
别****畜生畜生,
我剁了你。
杨五这才明白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,
用力的点了点头。
李灿然放开了捂住杨五嘴的手。
东霸天呐。
杨五没说话,
指了指前面的门房。
他住门房。
杨五还是没说话,
点了点头。
话问完了,
李灿然才发现老五还在认真地往杨五身上倒柴油呢。
哎呀,
别倒了,
错了。
现在李灿然的肠子每一根都气得生疼啊。
啊。
不是你让我倒的吗?
错了。
杀错了。
老五被李灿然骂得郁闷死了,
他自己认为自己一直在听李灿然的话,
而且一直在做正确的事儿啊,
凭啥自己就该被骂呢?
老五倔劲儿一上来,
扔下了柴油桶就走,
你给我回来。
李灿然现在连肝儿都气疼了。
老五就差没扯开嗓门喊了。
你究竟想让我干啥呀?
嘘,
你小声点儿。
房二和老五在房间里按住了杨五、
李灿然和提着另一桶柴油的土豆跳了出去。
李灿然认真地研究了一下那门房,
发现门房只有一个破旧的木头门,
而且那木头门下面还有个缝。
据说李灿然当时突发奇想,
不点天灯了,
改玩火烧赤壁了,
热得更有情趣,
这样才跟自己被放进冰窟窿里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
玩儿过火的都知道。
要是把柴油倒进一个接近密闭的房间里点着,
然后再燃烧了一会儿后,
忽然打开房门,
让氧气忽然大量涌入,
那绝对是有爆炸的效果。
很多人被烧死烧残,
都不是被文火烧的,
或者是烤的。
都是在情急之下,
一拉门被这爆炸似的火焰给弄得万劫不复的。
有很多人明知道这个道理,
但就是被火烤得求生不得,
求死不成,
然后心存侥幸打开房门,
结果可想而知。
大雨变成了暴雨,
门房屋檐下的土豆可比老五听话多,
一桶柴油不急不缓地倒向了门缝。
李灿然和另外一个人死死的拉住门把手,
怕东霸天闻到柴油味,
夺门而出。
转眼,
大半桶柴油倒了进去。
嚓嚓,
天空一声响雷,
土豆吓得一激灵,
手哆嗦了一下。
又是一道闪电,
又是一声春雷。
伴随着这一声春雷,
李灿然等人都听见了头顶处哗啦的一声脆响。
所有的人都抬头,
只有李灿然转身。
李灿然不但转身,
而且还在零点几秒的时间内摸出来腿叉子,
回手就向身后扎过去。
这一刀果然扎到了人,
但同时李灿然的脖子也是一领衣,
领子也被人抓住了。
李灿然为什么知道身后来了人,
而且能在转瞬之间就摸出了腿叉的回手一刀?
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
李灿然自己也不清楚。
或许这就是从他老祖宗那里遗传下来的本能吧。
别动。
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么一声暴喝。
天空又是刷啦,
一道闪电。
一个大的闪电,
起码能让地面亮上两秒钟。
在这个闪电下,
大家都看清楚了。
一个一丝不挂,
浑身都是雪白的肉的英俊男子的三棱刮刀戳在了李灿然的脖子上,
离咽喉只有几公分,
那刀已经磨进去了不少了。
而这个一丝不挂的男子的大腿根子处也插着一把刀。
这把刀攥在李灿然的手里,
刀已经磨进去了半根了,
血正从那个男人雪白的大腿上往下淌,
地上散落着好几块玻璃碴子,
他显然是从门房那根本没人注意到的一米见方的天窗上跳下来的。
这个男人当然就是东霸天。
轰隆一声雷过后,
整个院子又是一片漆黑,
谁都看不见谁的脸。
松开你的手。
东霸天那特有的拉着长长尾音的声音传到了大家的耳朵中。
三个数。
松开。
三。
ARM。
李灿然始终没做成。
白鸽。
出来。
养我。
出来。
看来李灿然是松开了手了。
门房的门咣的一声响,
陈白鸽出来了。
白鸽。
站我身后。
东霸天的语速永远不慌不忙。
又是一道闪电,
西郊的混子们都看到了,
暴雨中的一丝不挂的东霸天站在已经成了水坑子的泥地里,
刮刀顶着李灿然的咽喉,
东霸天的腿上。
插着李灿然的刀子。
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紧裹了一层床单的,
被暴雨浇的曲线玲珑的美艳女子。
这群西郊的土流氓,
什么时候见到过这样的女子?
个个都看的愣了。
据说西郊的那群流氓同时还都看见了东霸天胯下那东西,
居然此时还又粗又长又直的立着。
跟叉在腿上的那个腿叉子一样立着,
腿被扎了一刀,
还立着。
一阵响雷过后。
又归于黑暗。
东霸天开始发号施令了。
让他们出去。
我不杀你。
李灿然还是一言不发。
烦。
R。
东霸天不耐烦了,
直接开始数数了。
你们都出去。
李灿然相信东霸天敢一刀杀了他。
李老哥。
他不放你怎么办呢?
李灿然还没等说话,
东霸天接茬了。
我是东霸铁。
在斗殴中,
东霸天这三个字就意味着肯定不会占谁便宜。
都出去,
风儿老五也出来。
都出去。
大门开了。
人鱼贯走了出去。
东霸天发话了。
又是你呀。
好。
我夜袭你一次,
你也夜袭我一次。
扯平了。
你要是觉得咱们俩的恩怨还不能了,
那你甩个点儿吧。
李灿然默不作声。
你算是个在社会上玩儿的吗?
又来了一道闪电,
李灿然看到了东霸天那双带着鄙夷的骄傲的眼睛。
李灿然嘴角又抽了抽。
明天下午五点。
桥中间见。
谁不来谁是多棒。
对,
谁不来,
谁是犊子。
东霸天松开了李灿然。
滚吧。
李灿然转身就走了。
李灿然报复心太强,
在病床上就想把东霸天收拾他那一套东西加以改进,
重演一遍,
可是演砸了。
东霸天海。
杨无。
冯哥。
杨五从窗户跳了出来。
我整死你。
东霸天果然聪明,
连问都不用问就知道了,
刚才发生了什么事,
只要确定了杨武的方位,
一刀就扎了过去。
杨五对自己家的地形比较熟悉,
翻了墙就跑了。
他知道东霸天最恨吃里扒外的小人了,
现在暴怒中的东霸天说不定真敢扎死他。
东霸天光着身子,
腿上还扎着李灿然心魔的腿叉子,
没追。
陈白鸽不解呀。
你捅他干啥呀?
哼,
要不是刚才那声雷把我吓醒了,
现在咱们俩已经被烧死在门房里了。
那和杨五有什么关系啊?
哼,
他要是喊一嗓子,
咱们会听不见吗?
那你也不至于要扎死他呀?
哼,
我就是吓唬吓唬他。
哎呀,
快回房间包包,
一会儿一起去医院。
没事儿。
沉埋歌眼前的这个目光柔情似水的男人,
似乎跟在江湖上威风八面的那个东霸天是两个人。
我没事儿。
我自己去医院。
你好好在家休息,
肚子里的孩子要紧。
哎呀,
你比肚子里的孩子重要多了。
别瞎说。
你明天非要去跟他们打架呀?
为什么呀?
我。
恩怨总得有个了结呀。
陈白鸽就哭了。
那你要是出事了,
我和孩子。
东霸天沉吟了半晌。
我不会有事儿的。
第二天。
胡司令带着兄弟们到了杨武家。
东霸天在杨武昨天睡的房间里给大家开了个简短的会。
这次的会中,
东霸天没有表现出一点乖张,
更没有朗诵诗词。
胡司令等人都觉得奇怪。
西郊的这帮人可能比那卢松的手头还硬。
他们是真不怕死。
而且他们的身手也够好。
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姓李的。
就是在我弟弟厂门口一气儿捅了11个的。
知道了,
上次咱们不是收拾过他吗?
嗯。
那是在他没防备的情况下。
这样吧。
今天如果可能还是我跟他单抠。
还单扣啊。
霸天的兄弟们都愣了,
东霸天那一脑袋被卢松剁得扒拉,
还是粉色的道道呢,
还没变成白印儿呢,
居然就又要和李灿然单抠疯啦。
能单扣就单扣。
这事儿由我弟弟而起。
这是我的家事。
东霸天听说过西郊四丑的威力,
东霸天也知道自己的这些手下多数都是靠着自己的名头和手段撑腰,
虽然也有几个狠角儿,
但是就其凶悍程度来说,
跟西郊的那群猛农们比有差距。
玩群殴胜算。
不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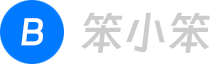 笨小笨
笨小笨














